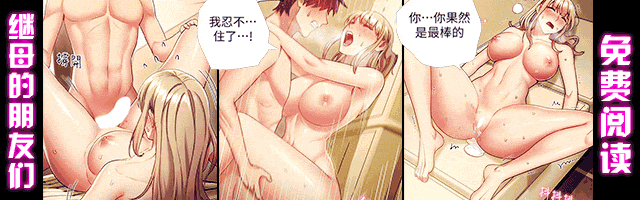萧乾向来纵容他,被宋祭酒这么急哄哄地推进营帐,他也不恼火,反倒坐下来,摊开纸拿起笔回信。
“快快哥哥快写,我还等着看呢。”
宋祭酒兴致冲冲地坐在他身边,捧着脸催促道。
萧乾满脸正经地点头,就提起笔,在白纸上画下一片梧桐树叶,悉心地勾完最后一笔后,他便收回手道:“写好了。”
盯着纸上的叶子,宋祭酒露出诧异的表情:“就这?”
“就这。”萧乾淡定自若的应声,而后把纸张折叠好,小心翼翼地放进竹筒,绑在紫钗的腿上。
“不是,哥、王爷好歹画了一棵树,你就给人回片叶子,你也太敷衍了!”宋祭酒揪起眉毛抱怨道。
萧乾闻言淡淡一笑,只沉声道:“他会看懂的。”
说罢,他便抱着紫钗,起身走出营帐,将抖着羽毛的苍鹰慢慢放飞。
对你的情,就如这片梧桐树叶,生生不息,总要多出一片才行。
瞅着紫钗越飞越远,宋祭酒真的是摸不着头脑,感到十分郁闷。
这两个人,到底在打什么哑谜哦?!!!
时辰到了傍晚,庭院里的热意褪去,只留下晶莹的水汽和一弯圆月。
偌大的寝殿中,站在桌前的男子正弯着腰,给面前的人把脉。
搭上那只白皙的手腕,摸到依旧古怪燥乱的脉象后,戚默庵皱了皱眉,觉得有些疑惑。
这些天每逢傍晚,他都会准时前来给裴玉寰煎药、施针,但三日过去了,对方的脉象却没有半点起色,当真是奇怪
“裴公子,近日可有不舒服的地方?”
迟疑半晌,戚默庵温声问道。
裴玉寰正专注地看着他,经他一问,身穿亵衣,散着银发的人摇了摇头,轻声答:“没有,已经好很多了。”
“那就好”得到他的回答,戚默庵便压下内心的疑惑,站起身道:“天色已晚,戚某便先告退了。”
“好”裴玉寰点了点头,用温润的双眸望着他,直到他离开。
走出宫门,踏着微凉的月色,在穿过水榭返回自己的宫苑时,戚默庵抬手整理一下衣袖,猛然发现自己落下了针灸盒。
“呼最近这是怎么了,总忘东忘西的”
他无奈扶额,想到裴玉寰那张恬静秀美的脸,心底莫名一阵悸动。
不知对方此刻是否已经睡下了?他睡着后,会是什么样子?想着这些让他心神不宁的事,戚默庵无奈地叹了口气,便返回去取针灸盒。
可这么一回头,却撞见了令他意外的情景。
“主子,今日这汤药还要倒掉吗?”
“倒了吧。”
“是”
回到寝宫门前,戚默庵刚要迈进门槛,却听里面传来了这番对话声,他下意识停住脚步,而后往裴玉寰所在的方向看去。
寝殿内烛火通明,裴玉寰正坐在桌边,手持药碗,将里面的药汁倒进了花盆里,待他倒完药,宫女便拿着花盆规规矩矩地退下,独留他一人略显清冷寂寥的身影。
目睹这一幕后,戚默庵唇角的笑意蓦然消失,方才莫名生出的柔情心思也瞬间烟消云散了。
“国舅既然不愿让戚某医治,那日直说便是,又何必在背后倒掉这些汤药,白白浪费药材。”
待他回过神来,竟已大步走进寝宫,站在了裴玉寰身边。
注视着药碗里的残渣,戚默庵心中倍感痛惜。
“戚大夫”裴玉寰正盯着烛灯发呆,听见男人的声音,他陡然惊醒,眼神有些茫然和无措。
戚默庵没有看他,只移开目光哑声道:“看来是戚某多事,给国舅徒增了烦恼”
他捏紧衣袖,停顿片刻,又一字一句道:“您放心,自今日起,在下不会再来叨扰您了,告辞。”
说罢,他转身就走,完全忘记了针灸盒的下落。
“等等!戚默庵,你别走。”
裴玉寰扬声叫住他,话音微微发抖。
听到他满含哀求的叫声,戚默庵心头一软,还是停下了步伐。
凝视着他的背影,裴玉寰站在原地,俊秀的脸上忽然浮现出一抹病态的红晕,迟疑稍许,他闭了闭眼,终是抬起手,缓缓解开亵衣的衣扣,露出白皙如玉的身体。
“国舅还有什么要吩咐的您,您这是做什么?!”听身后久久没有动静,戚默庵便转过头询问,可他刚一抬眼,就看见了裴玉寰裸露着上身的样子。
他当即红了脸,连忙后退半步,躬身拱手劝道:“夜寒天凉,还请国舅穿好衣裳,莫要着凉”
裴玉寰用一双清艳的眼眸看着他,脸烫的如同火烧,他犹豫片刻,而后转过身,背对着戚默庵道哑声道:“你抬起头,看看我
。”
“这,我”嗅到他身上隐约暗香,戚默庵紧绷着脸,心跳如雷。
虽说都是大男人,可面对裴玉寰时,他心底总会生出一股难言的柔情,连他自己都不知这是怎么了。
“这是什么?”担心裴玉寰受冻着凉,戚默庵没有再僵持下去,而是依照对方的话抬起了头。
可映入眼帘的景象却让他震撼不已:裴玉寰背对着他,衣衫半掩,银色发丝如瀑般倾泻在身侧,而他本该光洁完好的后背上,居然刺着一幅艳丽的牡丹绘。
瑰丽妖冶的牡丹图就像浸淫了情药的刺一样,横穿着裴玉寰白洁的肌骨,那是罪,更像是罚,给他纯洁的肉体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,让他沉沦欲海,又清醒低迷。
“这,这是谁做的?!还疼吗?”
分明是任何男人看了都会感到血脉膨胀的身体,但看在戚默庵眼里,只有愤懑和心痛。
身为医者,他当然知晓刺青的滋味并不好受,而如此肆意使用颜料,反复刺穿肌肤,所带来的伤痛更是难以想象,到底是什么人,敢这样羞辱折磨尊贵的国舅?
听到他的询问,裴玉寰双肩一颤,眼中流露出清浅的伤色:“他,他已经不在我身边了。”
“戚大夫,我并非有意倒掉你的药,只是,这刺在我身上的颜料,曾、曾淬过淫毒,每逢月中就会发作就算我尽力忍耐,身体依旧会变得虚弱。”
“如今的我,服再多的药,都是没用的,拖着这样千疮百孔的身子,其实,很早之前,我就已经放弃了。”
鼓起勇气说完话后,裴玉寰闭上了眼睛,不知该如何面对眼前的人。
然而下一刻,他的肩膀却传来温热的触感。
“戚默庵”他睁开眼,便看自己的肩上披着戚默庵的衣衫。
此刻他像一只受惊的小鹿,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能让他慌乱不安,而面前的男人就如避风的密林,将他牢牢护在臂弯,安抚着、宽慰着。
“夜深天寒,别着凉了。”戚默庵深深地看着他,又温声道:“您能告诉我这些,我很高兴。”
“敢问国舅,在您心中,戚某是否已经是值得信任的人了?”
裴玉寰闻声一怔,眼眶悄然红了。
“是。”
“那就不要放弃。”看见他眼尾的泪痕,戚默庵着迷地伸出手,帮他拭去晶莹泪珠:“因为我不会放弃,我会找到适合医治您的法子,我会,尽自己所能,让裴公子往后的日子,多一分快乐安稳,少一些病痛不安。”
“至于今晚的事,是我们二人的秘密,戚某绝不会告诉任何人,好不好?”
看着他认真的神情,裴玉寰的心跳得飞快,他没有半点犹豫,便握住戚默庵的手,无声的答应了对方的话。
这世上有一些人,好似山间轻盈的春风、似初夏飞落的繁花,又似奔腾不息的浪潮他们温柔美好到令人不敢触碰,生怕身上有一点肮脏,就会玷污了那份纯净。
此时在裴玉寰心中,戚默庵便是那风、那花、那浪,是他满心向往、又徒有余息的遗憾。
烈日炎炎似火烧,城楼外的沙场上黄沙飞扬,呛得人无法靠近,高耸的城墙上,樊小虞慵懒地倚在墙边,正百无聊赖地削着木剑。
“樊将士,不好了!萧爷呢!萧爷在何处?”
正在他昏昏欲睡时,城楼下突然跑来一名士兵,神色慌张的大叫道。
“萧乾带兵到城里巡逻了,有什么事?跟我说就成。”
樊小虞闻声站起身,擦去额头上的细汗,沉声道。
在校场摸爬滚打近半年,又经萧乾“管教”数月,眼下的他已然能独当一面,比以往成熟稳重了很多,这样的将领,自是能获得军中人的信赖,于是士兵也不遮掩,只道:
“咱们营里的兄弟,去郊外的山林探路时,又、又撞上黑煞阵了!所幸几名兄弟只是受了伤,可那阵法,实在是难破”
听完士兵的话,樊小虞陷入了沉思,对方口中所说黑煞阵,是红墨不知从哪儿搞到的机关,近些日子,只要他手下的兵一进林子探路,就会被歹毒的陷阱所困,死伤惨重,难以前行。
虽然胜券在握,但这么损伤人马也不是办法,还都是好兄弟想到这儿,樊小虞忍不住痛骂:
“他们这是穷没路了,只会搞一些阴毒手段!”
“樊将士,那叫穷途末路”士兵满脸黑线的提醒道。
“呸!小爷管它是什么路呢!赶紧给我找解决的法子!”
面对他焦急的面容,士兵低下头,想了想后开口道:“或许有人能解这阵法”
樊小虞双目一亮:“谁?”
“岭南四大家族之一,墨家如今的掌门人,墨诩笙。”
“墨家?那不是萧乾他”樊小虞呆了呆,半
天才反应过来。
“正是萧爷亲娘的家族。”士兵接过他的话,又沉声道:“当年修葺岭南神坛,墨家便造就了世间最难破解的机关暗器和阵法,想来这区区黑煞阵,对墨诩笙来说,应该易如反掌。”
“樊将士,咱们要不要给萧爷说一声,让他给陛下写信,求墨家啊!樊将士你打俺干啥!”
他话还没说完,樊小虞就给了他一个爆栗:
“你是不是傻,萧乾那么好面子一人,怎么可能给解大不,咳咳,怎么可能主动给陛下写信求援?”
“那咋办?”
“纸,笔,掏出来,我来写。”樊小虞板着脸,极力掩饰着自己不自在的表情,哑声道。
“不成,你来写。”
待士兵取来纸笔,他猛然想到,自己认识的那几个大字还不足以说明这等复杂的情况,便有点窘迫的下令。
“哦咋写啊?”士兵趴在地上问他。
“写给陛下的,正、正式一点就行了。”
“得嘞,您瞧好吧!”士兵写明军中近况,留下求援的话后,便准备把信叠起来寄走。
“等等!”此时樊小虞却拦住了他。
“樊将士,咋的啦?”
“本帅问你,那个咳咳嗯!哼!念你两个字,咋写?”樊小虞不自在的问道。
即便努力克制,却仍抵抗不了内心的思念,说他幼稚也好,没规矩也罢,认了!
“您要再加上‘念你’俩字?”士兵奇怪的发问。
“嗯,加上。”樊小虞粗生粗气道。
“俺来帮您写”士兵也不多问,埋头就写。
“谁让你帮我写的?”樊小虞又给了他一锤,掰了根木棍给他:“你,地上写,我学。”
“哦得嘞!”士兵不想再被打了,赶忙接过木棍,任劳任怨地教他。
于是乎,那张不大不小的信纸上便出现了两种字迹,一种字虽称不上整洁,起码能让人看懂,只有信尾的俩字,歪歪扭扭,丑的离奇,丑的让人发笑。
解天收到信件时,正在御书房听大太监施盛禀报宫里的大小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