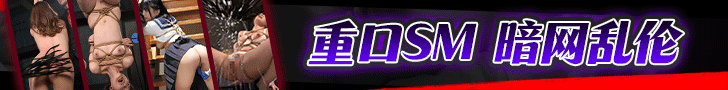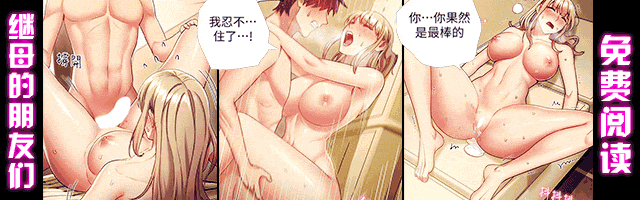使君子要到朝廷议事,封对月送他出门后打算回房间,婢女将油了新漆的瑶琴递给他,“夫人,琴油好送来了。”
封对月点点头,接琴看成色。
他看的专注,而在下人的眼里,那从不露面的夫人美目半敛,本就生得极美,额间一点红朱砂,抱琴而立犹如画中仙子,她不禁晃了神。
她们夫人很少开口,温温婉婉从不苛刻,与主子的感情又好,相濡以沫被下人奉为佳话。
但是只有近身服侍的她知道,他们夫人是个双儿。
双儿也好,主子信任她将夫人托付给他她。如今夫人已经有孕四个月了,小腹微微隆起,她心疼那削弱的身子以后不知道要被胎儿压得怎样沉重,一抖披风说:“夫人,回房吧。”
封对月一直在那瑶琴的新漆,听了婢女关心一弯眼睛,点点头。
他如今扮做新妇打扮,不宜有太多肢体动作,抱了琴要回房。
突然听见门口轮轴声。
“大人回来了?”婢女睁圆眼睛说了他想说的。
封对月也是疑惑,他知道翰林大人今天要议政,没想到这么快回来,这个点,应该刚到皇宫才是。
门口有人声,他疑惑着出门迎接,脸上虽然轻纱蒙面,纱面下梨涡浅浅,配上发髫俨然是娇俏的妻子形象。
只是他还没走完回廊,外面那人已经阔步走了进来,他只是透过绿丛看了一眼,就大惊失色。
“夫人?”婢女听见旁边的惊吓吸气,回头问,见那无论何时都恬静温婉的美人倏的变了脸色,猛地回身。
封对月见了那黑袍之人就要躲,听见旁边侍卫说:“前面的,站那。”
他被叫住,绿植掩映外面应该看不清什么,他不敢回头,但更不敢抛开,左右一望,将婢女拉进柱子后面,忍着颤抖说:“何事。”
一开口,嗓音空灵温婉,比女人还女人。
因为他小时候学过变声之术,才能游刃有余地在府中扮演新妇,但饶是声音平稳温婉,他的身子却像回想起什么一样惊颤。
他死命攥着衣服,听见侍卫说:“唤你,你为何还要躲。”
封对月拿着女音说,“因我是新妇,过门未足三月不能与男子见面,何况……”他嗓音带了委屈说,“是外面的人。”
那侍卫带了点敬意说,“原是使大人的夫人,冒犯了,”封对月听见佩刀作揖晃动的声音,那侍卫继续说,“我们主子是使大人的同僚,外出散心途经此地,听闻是大人府邸前来拜访。”
封对月半信半疑,一直未有什么风声似乎无需警惕,但是正好上门又让他觉得太过凑巧,他拿捏不定,只能做戏:“夫君不在,你们于花厅等候,我一介妇人,实在不能多谈。”
“这……”那侍卫的声音踌躇了,似乎在等人指示。
这时封对月听到另一道声音说:“你,会弹琴吗?”
封对月一听那熟悉的低醇嗓音,身子犹如过电一般,等婢女拉他他才回过神,冷静下来说:“略懂。”
那人说:“弹给我听。”
封对月声音大了些:“我一介妇人,如此不合适……”
“弹给我听,”那人重复了一遍,口吻总是那么刚愎自用不容置喙,话尾音调却降了几分说,“我累了。”
“……”封对月对他这种脾性感到无力,再三拒绝又怕其追究,看其反应,确认是没认出,便说,“请于花厅等候,妾准备好了再命人通知。”
……
使君子走到约莫北门的位置时,遇上续断。
“丞相。”
“学士。”续断回礼。
两人平时尽可能做出生疏的样子,不想让人得知彼此关系亲密,而此时碰巧遇到倒也不必多么遮掩,如常交谈。
续断说:“学士,陛下几日不朝,今日却将我等召来议政,如此勤政岂不奇哉。”
使君子说:“圣心所思,臣揣度不到。”
续断浅笑,“也是”,在北门士兵面前故意对使君子说,“学士,请。”
使君子低了半寸肩膀说:“自然是丞相先请。”
两人往北门过,一架没有标记身份的马车与他们擦肩而过。
等马车过了使君子见续断停下来,问:“师……丞相,可有何事?”
续断看着那马车扬起的沙尘说:“学士,你可看到了?”
使君子看着那车尾说:“那马车极其普通,有什么奇怪之处吗?”
续断仍是对着那方向,说:“那马车,无官衔标志,无军事印刻,是辆‘无牌轿车’。”
使君子想了想,表情也凝重了起来,“非官非兵,却能在皇宫出行,那车内那人,会是……”
他思考着,听见续断回过头来问:“学士,你认为陛下为何让我们聚在一起议政。”
使君子沉思,“让我们聚集在一起,是想让我们会首,又或者……”使君子猛地抬头,“他想去见谁!”
续
断点头,凝重说:“最怕是这样。”
……
封对月调弄琴弦,这偏厅是席地而坐,上首设置了矮桌,与下位隔着屏风。
厅内只余二人,他按那人说的,挑擅长的弹。
他却不敢出头,每数十音符错漏一拍,将一身精妙琴艺弹出差强人意的的效果。
又一曲完毕,他调着琴弦,屏风外那人问:“接下来是清平令吗?”
封对月指尖顿了一下,仍然拿着女音说:“是。”
便敛眉将前奏弹起。
此时起步低缓,那人问他:“学琴多久。”
封对月跳了一律,再将指法放慢对上正确乐谱说:“三年。”
学琴超过十年,但只能说三年。
“三年,”屏风外那人听不出情绪,似是无聊而问,“可还会别的乐器。”
“只擅琴。”
“可曾从师。”
问题有点多,封对月分心答:“拜过两位师父。”
“原籍是哪里人。”
封对月背道:“东丘。”
“最喜欢哪道乐谱。”
“《九韶》。”
“和使君子认识了多久。”
“四个月……啊、”
“啊、”琴弦断裂,封对月后仰着手心撑地。
“四个月,”察觉屏风后那人冷笑,“听闻使君子的夫人是东丘的商人女儿,中举后迎娶进门,”男人扶着膝盖站起来说,“认识四个月的青梅竹马,是吗?夫人。”
那人走近屏风,说:“九韶是宫廷秘乐,商人的女儿却有这种见识吗?夫人。”
封对月哆嗦,“那是因为,是因为……”
他还未答出个所以然,男人说:“让我先说吧。”
封幌看着屏风后那影绰人影,摸着屏风上熟悉的画法说:“夫人,我认识一人,他学琴超过十年,精通琴、陨,笙和鼓也略懂。”
他嘴角勾起些浅笑说:“他拜过两位师父,真巧,他最喜欢的乐谱也是九韶。”
“更巧的是,”封幌眯起眼睛,“他与使君子也认识四个月,而在他们认识第三个月的时候,他就嫁给了他。”
封幌指尖几乎将屏风抓破说:“我们相伴十八年,他却在和别人认识第三个月的时候就嫁给他!”
他将手从屏风上扯开,手摁在腰间佩剑上说:“让我见下你吧,夫人,你刚才弹的琴甚合朕意。”
“不!”屏风后那人惊叫,“你站那处,且听我说。”
“要说,当然要说,”封幌从腰侧拔出佩剑,呲啦一声脱离刀鞘发出刺耳响声,他说,“但等我得见夫人,再说!”他高举佩剑——
“不行!”
长臂一挥,屏风轰隆一声,“啊!”
屏风后那人惊叫,约两米宽的百鸟绘屏轰隆倒下,露出后面仓惶人影。
封幌眼中有憋狠了的期待,欲望蛰伏得太久让他像红了眼睛的野兽,他那饥肠辘辘的视线投向琴桌那人,却在看到那人时泄了气。
“你……”封幌一顿,随之狠狠皱眉,“你是谁!”
屏风后那女子匍匐到他脚边哭说:“妾本是乐伎,蒙翰林大人不嫌弃才纳入府中,改头换面也是为了此等缘故,请大人不要声张,妾爱惜夫君的名声。”
封幌看那明显不是他要找的人咬紧牙根,半晌后将桌子和瑶琴一起踢翻。
他将佩剑扔在地上,一秒都不愿停留地快步走出。
“大人息怒!”乔装打扮的婢女头伏得更低,等整个房间彻底冷清下来,她抬起头,确定那可怕的黑袍男人走了之后她哆哆嗦嗦直起身,连挪带爬地去拉背后的门,“夫人!”
她刚才从那人的言辞中惊恐发现,那人竟是大封的君王,而他们夫人,竟是君王在找的人。
她又惊又恐的去看他们夫人,见那屏风之后的小隔间,他们夫人抱着膝盖坐在里面,低着头看不清情绪,而桌子上面,那台瑶琴断了好几根琴弦。
……
使君子赶回家之后得知封对月在亭子,他越过环廊一把将那人抱住,“月儿!”
封对月正失神,猝不及防被抱住,他吓了一跳,推开使君子说,“你回来了。”
使君子追着薄纱摸封对月脸颊说:“月儿,你没事吧?”
“……”封对月躲开使君子的手。
使君子手失了着落,顿了一会收起,坐在封对月旁边说:“月儿,师哥和我说,他可能会来和你见面,而你,可能会变得很奇怪,他没办法过来,所以让我来问问你。”
他坐在封对月旁边,夫妻二人各自看着前面,使君子说:“月儿,我能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么?”
封对月说:“月儿什么都没想。”
使君子听了,眼神一动,有半晌没有出声,接着才说:“他已经将你心境打乱至此了么。”
“没有!”封对月转过来看着使君子,却不知道在对谁生气一样
说,“我没想他,什么都没想,我什么都没想还不够么!”
使君子皱眉说:“你什么都没想,是因为他将你思绪搅得一团乱,你什么都思考不了。”
“别说了!”封对月受不了叫道,他捂了耳朵又放下来说,“我没跟他见面,我也没想他,我很冷静,你不必过问我!”
使君子抓住他的手说:“月儿,你听我说。”
他让封对月对着他,说:“月儿,你已经嫁给我了,只要你坚定些,就算是他也没办法干什么。”
“不可能!”封对月的情绪像延迟的浪潮那样慢慢卷了起来,似乎刚才冷静应付那人不是他一样, 他的情绪波动越来越大,他叫道,“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!”
“月儿!”使君子用力抱住他的臂膀,“你已经脱离他的掌控了,不要一看见他就这么慌张。”
他安抚道,“我知道你最近情绪不安稳,但你这样,”使君子怅然道,“只会让我觉得,你还一直受着他的影响。”
“我没有!”封对月条件反射道,“我才没有受他影响,他是那样一个人,我早就和他没有关系了,就算他进来的那一刻,我也没有露出马脚,就算他问话,我也能和他对答,就算他靠近,我也没有躲,就算他认出我,就算他……就算他……”
他说着,眼眶红了起来。
“你真的没有受他影响吗?”使君子反问,“如果你真的没有,为什么你不敢见他,为什么婢女跟我说,你今天躲在隔间里面?你不能见他,不是因为你做不到吗?你刚才哭现在哭,难道不是因为你还想着他吗?不是吗!”最后一句质问,使君子说的很大声。
“不要说了……”封对月哭咽着肩膀颤抖,他像对着使君子又像对自己说,“我只是最近情绪不稳,和他没有关系,我明天就好了。”
“我知道的,”使君子眼眶也有点泛红,“即使我把别人也一起给你,新婚那晚,你还是抱着自己,宁愿一个人。”
那天晚上,使君子醒来,手边空落落,当时他只是觉得失落,但是当他翻身,他看见床中央有一团小小的身影,他才知道他谁都不想选择,越觉得心寒。
封对月摇头哭说:“我没有……”
使君子抚摸他掉泪的脸颊,认真问:“月儿,你真的没办法,忘记他吗?”
“我忘了!”封对月几乎是哭叫,“我早就忘了,一个,不将他人尊严放在眼中的暴君,一个,将自己孩子生命视同草芥的凶手,谁会爱他?我不爱他!”
使君子见他这样眼神颤动还拼命自证的样子,不由得皱起眉说:“你不爱他,为何一直不能接受我?”
他将他扯近了问:“你不爱他,为何我们新婚一月有余你仍以怀孕为借口拒绝我?”
他越想越气,眼睛染上怒色抓着那人下巴说:“如果你真的不爱他,那么就在此处,请你想起你使夫人的义务,在这里服侍我!”
他逼视那惨白着脸色的太子说:“你做不到吗?”
他带来愠怒说:“使夫人,你做不到吗!”
他说着将封对月往后一推,两人貌合神离的夫妻假象也散个稀碎。
如果没有今天的意外,如果没有此刻的交谈,他愿意一直装傻下去,可是已经连别人都察觉到了,丞相跟他说此下的平静可能会被打破,婢女言辞躲闪地说来了一个夫人很在意的人,他没有办法再装傻,他知道这个人一直在勉强当他的妻子。
他就算是把别人捧到他面前,他还是对那个人留有念想,不敢面对只能把自己藏起来。
使君子双手紧握,用力得手背都浮出青筋,他像是一颗沉静的炸弹,因为平日很友好所以此刻更显得反差。